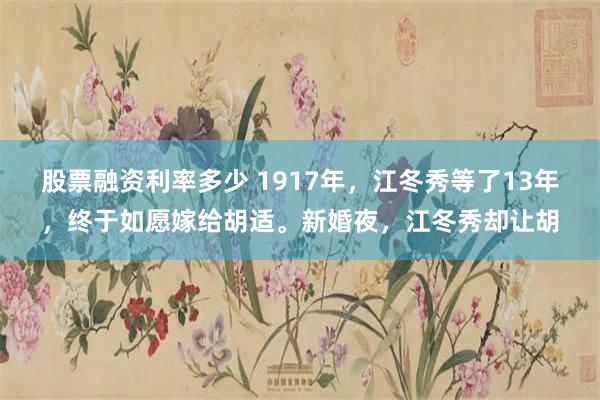
1917年,江冬秀等了13年,终于如愿嫁给胡适。新婚夜,江冬秀却让胡适睡地上股票融资利率多少,胡适问:“难道不用圆房吗?”江冬秀说:“您不当我是妻子,我何必让你做夫君呢?”
1904年,胡适刚满十三岁,家里就为他定下了婚事。对方是同县人家的一位姑娘,名叫江冬秀。胡家当时还不算富裕,但胡适聪明勤奋,被乡里人称为“未来的读书人”。
江冬秀的家人听闻后十分满意,一锤定音,把两家绑在了一起。
江冬秀比胡适小两岁,那时还扎着羊角辫。听说要嫁给一个读书人,心里既好奇又羞涩。可她从未见过未婚夫。
村里人提起胡适,总说他“脑瓜灵活,笔头利落”,江冬秀听了,偷偷在灶台旁问母亲:“我什么时候能见他?”母亲笑着拍了拍她的头:“等你长大了。”
定亲后,胡适离开了村子,先去了上海,后来又远赴美国留学。这一去,就是十三年。江冬秀的日子,却如同一口慢火的锅:每天学针线,帮家里干农活,听长辈念叨“等胡家少爷回来”。
等的日子不容易。村里有人嘀咕:“未婚夫那么久没回来,还能记得她吗?”江冬秀不说话,但心里开始犯嘀咕。
她问母亲:“如果他忘了我,怎么办?”母亲还是那句话:“你等着,他是读书人,读书人讲信用。”
可江冬秀渐渐明白,不能光等。她学会了缝补,也跟着邻居学做菜。她心想:就算日后成了胡家媳妇,也得有本事让人瞧得起。时间让她变得沉稳,也让她多了几分冷静。
1917年冬天,胡适终于回到了家乡。父母催促婚事他点头答应,长辈们说:“你这未婚妻可是等了你十三年,你可不能让她受委屈。”胡适听着,只是笑没多说话。
婚礼定在12月底,江冬秀穿上大红嫁衣,坐上轿子,一路上锣鼓喧天,鞭炮声震得人耳朵发麻。她低着头,手里握着帕子,心里却很平静:这一刻,等了太久。
到了晚上,送亲的人散去,新婚夫妻终于独处。胡适卸下长袍,坐在床边。他轻声说:“这一天够热闹了,现在可以歇歇了吧?”
胡适愣住了,眼里带着疑惑:“这是闹的哪一出?”江冬秀站直了,语气平淡:“您读书多年,从没提过我,不认我是妻子,怎么让我认您做夫君?”
这话说得掷地有声,胡适没想到这个他从未谋面的姑娘,竟然如此直白。他没有生气,只是低头想了想,起身拿了条被子,在地上铺好,说:“那今晚就依你。”
没有常人想象中的温情,也没有任何浪漫。屋子里只剩下灯芯燃烧的轻微声响。江冬秀躺在床上,闭上眼,心里却没有半点懈怠。这场较量她赢了,她知道这只是开始。
胡适睡在地上,心里却比白天还清醒,家乡这位小女子会有如此刚硬的一面,躺在冰凉的地板上,他突然觉得,这场婚姻或许不是那么简单。
江冬秀进了胡家门,成了名义上的胡家媳妇,可日子却一点都不轻松,胡适虽然表面温和,对谁都笑呵呵,可骨子里似乎有些冷淡。
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,埋头写文章或读书。家里出了点小事,他最多点点头却从不插手。
江冬秀可不是那种好糊弄的女人。她逐渐掌握了这个家的一切,从伙食到家务,从佣人到亲戚,样样都管得井井有条。
她烧的一道徽州“一品锅”成了胡家的招牌,胡适吃着她做的饭,偶尔会笑着说:“这锅里有家乡的味道。”
可两人的矛盾依旧不可避免,江冬秀发现胡适这个丈夫并不按常理出牌,除了书和报纸,他似乎对什么都兴趣寥寥,江冬秀有时会忍不住抱怨:“你读书归读书,可这日子总得过吧?”
胡适低头不语,江冬秀等了他十三年,成了他的妻子,如今又挑起了这个家的担子,可他的心思总在远方。
在美国留学的那些年,他见过太多自由、开放的生活方式,而这场从小被安排的婚姻,总让他觉得有些拘束。
两人的争执一来二去,却没有真正撕破脸。胡适性格宽厚,吵架时总让着几分,江冬秀也明白,闹归闹事归事,她始终把家里的大小事务处理得妥妥当当。
江冬秀的泼辣,不只是性格里的直爽,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,她不只是会管家、会做菜,更懂得如何在这个家里立住脚。
她学会了写字,每天在小本子上记账,她陪胡适出门,听他说各种书本上的道理,却总会点头微笑。
胡适在家里写文章,突然发现江冬秀在一旁认真地模仿他写字,他问:“你学这些做什么?”江冬秀头也不抬:“你读书,我识字,省得将来总被你看扁。”
1930年代,胡适在学术上声名大噪,成为一代文化巨匠。江冬秀始终在家里为他守住一个安稳的港湾。胡适曾经感慨:“这个家,若不是她,早散了。”
江冬秀也变了。从那个直言“您睡地上”的姑娘股票融资利率多少,变成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。她不再刻意去跟胡适争个高下,而是用行动证明,自己是这个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配资股票平台_实盘配资平台_鑫东财配资观点






